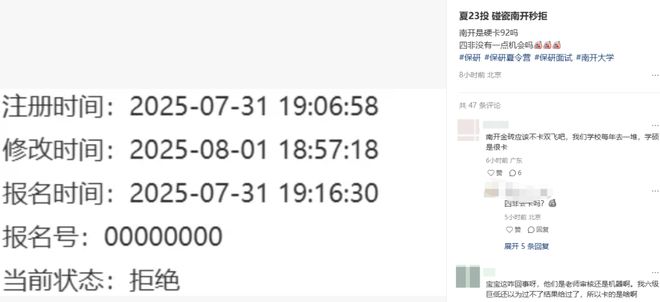linkloud 引言
今年上半年最戏剧性的 AI 收购案非 Windsurf 莫属。 最初,市场传闻将被 OpenAI 收购。最终,创始人及管理层部分成员加入谷歌,剩下员工及业务被另一家 Coding Agent 公司 Cognition 收购。
前段时间,20VC 与曾主导投资 DocuSign、Box 等 SaaS 公司的 Scale 合伙人 Rory O’Driscoll,和 SaaStr 创始人 Jason Lemkin,就这个话题展开了精彩对谈。在 OpenAI 以 30 亿美金收购传闻兴起后,AI 公司与 SaaS 的增长与估值逻辑究竟有什么不同?以及当前个人投资者与机构化 VC 面临的根本性差异与生存法则,还有基金的 LP 在这个“疯狂”市场下面临的“困境”,Enjoy!
一、AI 巨头的战略布局:从收购看市场
1. OpenAI 的 30 亿美金豪赌:一笔合乎逻辑的收购
几个月前,关于 OpenAI 计划以 30 亿美金收购 Windsurf 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
这笔交易虽然最终并未达成,但它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假如你是 OpenAI,发现自己的产品有两三个巨大的 Use Case,那么自然希望在这些关键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其中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就是 Coding。在 Coding 这个方向上,通过收购来补强自己的能力,用自己市值的 1% 去做这样的收购,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一个宏观的视角。还可以深入探讨更多细节,比如他们是否也曾尝试收购像 Cursor 这样的公司等等问题。但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对于一家市值高达 3,000 亿美金、业务建立在一系列不同终端应用场景之上的公司来说,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应用场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理所当然的战略选择。
OpenAI 已经明确表达了其强大的企业意图:必须在 AI Coding 这个领域拥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产品。即便这次没能收购 Windsurf,等在 OpenAI 办公室门外的其他 AI Coding 公司的队伍,恐怕会长到绕过整个街区。在某个时间点,他们总会买下某家公司。
2. 从收购规模看战略决心
从收购的规模来看,我们可以从大型科技公司的并购历史中学到一些规律。不同级别的交易意味着不同的战略决心:
就像 Adobe 曾经想要收购 Figma,或者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这不仅仅是某个 SVP 级别的决策,而是 CEO 亲自拍板说“我要押上公司的未来”。这样的决策确实是在赌上一切。
这是某个业务单元的负责人说“我要为我的业务单元赌一把”。具体到 OpenAI 的情况,他们在 Coding 领域相较于 Anthropic 确实略显薄弱。Anthropic 在开发者社区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所以,用市值的 1% 来追赶这个差距,在当下几乎是不易察觉的成本。当公司处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时,这种 10% 或 1% 门槛的赌注,是必须去做的,因为时间不等人。
对于 OpenAI 来说,他们要么彻底放弃这个市场,要么就必须进行这次收购,以追赶在开发者社区和拥护度方面遥遥领先的 Anthropic。他们可能无法收购 Cursor,因为后者刚刚完成新一轮融资,估值太高,而且可能也不愿意出售。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选择。
3. 没人知道未来,但总有人在下注
我们要认识到,人的思维通常局限在当前的数量级,很难想象高出两个量级的情景。然而,对于那些市值已达 3,000 亿美元的公司而言,它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仅有的三四家两万亿美元巨头之一,并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回顾过往,微软为了打造 Microsoft Office,收购了像 PowerPoint 这样的公司,当时付出的稀释成本如今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当年的搜索公司 Excite@Home,他们认为必须将搜索与底层的管道结合起来,于是与有线电视基础设施公司 @Home Network 合并,结果却成了一笔愚蠢至极的交易。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当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时,做一些分散的押注可能是最好的策略。如果审视 OpenAI 这次针对 Coding 领域的特定押注,会发现这与过去一年 AI 领域的叙事演变非常契合。
一年前,主流的看法是“模型就是一切”,所有的 AI 应用都只是模型的“套壳”。后来,风向又变成了“模型是商品,AI 应用才是一切”。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第三次迭代:拥有巨大市值的模型公司,反过来可以收购应用公司。这再次印证了一点: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会怎样。
4. 收购背后的长期影响
客观来看,Sam Altman 的一个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他有强烈的“行动偏见”。他看到 AI 有两三个大的应用场景:第一个是直接聊天,已经完成;第二个是 Coding;第三个是 Customer success 等等。他就像在逐一完成一个待办事项列表。在 Coding 这个关键节点上做些什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OpenAI 即便收购了 Windsurf,他们也不必采取残酷的 Salesforce 或 Oracle 式的策略,即“要么用我们的,要么什么都没有”。他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平台,让客户自己决定。他们可以说:“这是由 OpenAI 驱动的 Windsurf,我们将投入 1,000 名工程师让它成为最好的产品。但如果你想用 Cursor 或其他任何系统,我们同样支持你。”很多公司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让不同的团队和产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
当然,不必在短期内表现得无情,但平台方终究拥有一种“磨损”的能力。回顾 PC 战争的 20 年,最终在个人生产力应用领域,独立于微软而大规模销售的公司只剩下两三家,比如 Adobe 和 Quicken。所以,如果 OpenAI 收购并极力扶持自己的 Coding 工具,那么对于其他独立应用来说,这将是一场长达十年的艰难磨砺。
二、资本洪流下的 VC 新常态
1. VC 的变局:多阶段基金挤压下,种子基金何去何从?
Windsurf 的股权结构也值得关注。它的种子轮是由 Neil Mehta 的 Greenoaks 领投的。这恰好印证了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即多阶段基金在种子期的表现非常出色和高效。他们的资本成本极低,以至于在种子阶段几乎压倒了所有专门的种子基金。Greenoaks 领投 Windsurf,并持续在 AI 领域加倍下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对于一个规模在 15 亿到 30 亿美金之间的基金来说,单笔交易的回报能有多大份量呢?据报道,Windsurf 这笔交易的回报大约在 5 亿到 6 亿美金之间,仍然不到基金规模的三分之一。
需要多少个这样的 Windsurf 才能让一个基金获得 5 倍的回报?答案是 15 个。这对任何基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话说回来,当真的能兑现一张 5 亿美元的支票时,终究是乐意收下的。毕竟在这个行业里,能将投资成功变现才是硬道理。
然而,种子基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当多阶段基金进入种子轮时,它们会稀释种子基金经理的持股比例。如果你作为一个种子基金经理,为了一笔交易只能争取到 2-3% 的股份,而不是过去的 12%,但基金规模又翻了一番,那么投资结果也必须翻倍才能维持回报。这给种子投资带来了复合的风险压力。
过去,一个 10 亿美金的退出就可以让一个种子基金获得丰厚回报。但现在,对于许多种子基金经理来说,这可能已经不再成立了。一个 10 亿美金的独角兽项目,甚至可能无法让基金回本,更不用说实现 3 倍的净回报了。如果独角兽都无法回报基金,这对种子投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每个阶段都在挣扎。证据就是,每个人都在向其他阶段“漂移”,说“天哪,我需要做那个才能让我的模式运转起来”。这导致了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没有人停留在自己的“泳道”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超级大基金什么都做,这些“全栈服务商”让其他所有人都开始质疑自己的定位。
这种资本过剩也带来了另一个现象:稀释敏感性。如今,种子轮的融资稀释比例通常被压缩到 10% 左右,而在过去,这个数字可能是 15%。当资本充足,街上有三家基金排着队给你更好的条款清单时,企业家自然可以对稀释更加敏感。但当资本变得稀缺时,获得更好的所有权就会容易得多。Barton Biggs 曾说过一句名言:
“没有哪个好生意是过剩的资本无法摧毁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2. 百倍估值与闪电增长:AI 时代的新范式
谈到过剩的资本,就不能不提当下的估值。最近,一家年收入只有 700 万美金的公司,竟然以 70 亿美金的估值完成了融资,这相当于 100 倍的收入倍数。这不禁让人感叹,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那个疯狂的时代?
现在,投资人又开始重新为 AI 公司的高增长付费了。关键问题是,他们这次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增长吗? 那家 700 万收入的公司,明年能增长到 2,000 万或 3,000 万吗? 如果能,那么你的投资在一年后就变成了 6 到 10 倍的收入倍数,虽然过程惊险,但并非不可行。但如果增长放缓,显然就是搞砸了。
我们是否身处一个全新的世界? 像 Klaviyo、UiPath、ServiceTitan 这样的公司,都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百万美金的 ARR,在“想法的迷宫”里摸索了很久。而今天,是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必须全速前进,再也没有五年时间可以迂回前进?
似乎现在的模式是,在找到 PMF 之前,那段“早期探索阶段”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五年。一旦你锁定了 PMF,轨迹就完全不同了。过去 SaaS 的轨迹是锁定的,增长是稳定可预测的。而现在奇怪的是,一旦你锁定了 PMF,就像前面提到的,可能在 90 天内,一家一年前还被认为不会成功的公司,突然就要拒绝 30 亿美金的估值了。这就是今天与 SaaS 时代最大的不同。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产品传播迅速,人们接受度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 AI 这个奖赏值得去争取。如果你比较不同技术浪潮的炒作程度,无论是 PC 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AI 的炒作程度都比它们加起来还要大。
还有一个因素是“Early adopter(早期试用者)”效应。世界上几乎每一个 Early adopter 现在都在积极寻求部署 AI 工具。2021 年到 2024 年期间,可能无法让这些人关注到任何新东西,因为他们太忙了。但现在,100% 的 Early adopter 都在市场中。这种增长虽然疯狂,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所有 Early adopter 同时入场的时刻。
此外,这些 AI 产品通常非常便宜。如果你不大量使用,Windsurf 每月只需 20 美元。这不是一个需要销售团队介入的 20 万美元的企业订单。低廉的价格让采用变得毫无风险。当一个工具只需要 20 美元时,每个 Early adopter 者都会想:“为什么不试试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惊人增长水平的原因之一。
3. AI 商业模式的悖论与新机会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 AI 能让公司的运营变得如此便宜,甚至可能催生出单人运营的 10 亿美金公司,那么为什么融资轮次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答案很简单:首先,VC 总是想投资那些实际上并不需要他们资金的公司。其次,随着估值的膨胀,今天的创始人们对稀释和风险变得完全不敏感。当估值达到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金时,他们看不到其中的风险。这种心态,加上 VC 渴望参与热门交易的组合,导致了公司会吸收大量资本。VC 们想投资资本高效的公司,但他们却想用一种资本低效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另一个正在兴起的模式是 AI 赋能的并购游戏(AI Roll-up)。在法律、会计、房地产等领域,一些公司通过收购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公司,然后用 AI 技术进行改造和赋能。这种模式是否可行,目前还存在争议:
五年前,我们看的每个项目可能只有两三个竞争对手;而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 10 到 15 个。不过,在真正的 ToB 领域,尤其是解决复杂大问题的领域,创新并不像中端市场(Mid-market)那么多。想要构建下一个 ServiceNow 的团队并不会太多。
此外,垂直 SaaS 领域仍然投资不足。AI 的浪潮才刚刚开始触及许多垂直行业,在这些细分市场里,通常不会看到动辄 500 个竞争对手,因为深度的市场专业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壁垒。
三、人才、LP 与机构的困境与抉择
1. 人才的流动
Windsurf 的投资方 Kleiner perkins 也发生了一件很出名的事:其合伙人 Bucky 离开后宣布加入 Lightspeed。这又是一个优秀年轻人离开大品牌基金的例子。这背后反映了 VC 行业内部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问题。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如果你在一家风投公司里手气很好,但并不是管理公司的人,那么离开去创立自己的基金可能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Redpoint 的 Tomasz Tunguz 筹集了大约 7 亿美元的基金后也曾表示,他应该早点这么做。虽然 Redpoint 很棒,但他作为一名独立的 GP 管理着近 10 亿美元的资产,这在经济上可能远比在一家大公司拿着几十万到一百万美元的年薪,然后等待 22 年才能拿到一些 Carry 要好得多。当你在别人的基金里创造了 10 倍的回报,却不能参加管理会议时,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
关键在于,当有一个优秀、有才华的年轻合伙人,他们做得很好时,作为领导者,如果不能尽快的把他们“拉拢”,那一定是不明智的。运营良好的公司会确保表现好的人得到提升和分成,这是他们的工作。
人们离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候是因为做得很好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有时候则是因为虽然自己做得很好,但公司的其他人都亏了钱,无论未来五年多么努力工作,都只是在为别人填坑。
这种来自 A 级公司的分拆潮,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一直是这个行业的本质,现在也没有理由改变。尤其是在经历了五六年的繁荣,然后又遭遇了流动性缺口和估值下调之后,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年轻、积极进取的合伙人可能会审视公司最后两期基金的状况,发现即使自己表现出色,整个基金的回报预期也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就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
与此同时,LP 的态度也很有趣。他们仍然想投资这个资产类别,一方面想投资新成立的公司,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人才正在流失的同一家老牌公司投入巨额资金。这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动态。LP 们看着那些大的平台型基金,觉得别无选择,因为那是唯一能大笔投资的地方。但他们又感到害怕,所以为了早上起来感觉良好,他们决定也投一些年轻的新秀。于是,他们把 2 亿美金投给大公司,再给新人 2,000 万美金,这样感觉很好。
这种“杠铃效应”:资金要么流向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平台型基金,要么流向全新的小型基金,确实存在。但最终,决定一切的还是业绩。无论你是大、中、小基金,只要表现好,市场总会有用武之地。正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2. LP 的困境与捐赠基金的危机
尽管那些从大型、顶级基金公司出来的明星管理者很受欢迎,但实际上现在并不是一个出去为新基金募资的好时机。LP 对新基金的胃口普遍很低。与 2021 年大量新基金涌现的情况相比,现在成功募资的基金数量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是来自顶级公司、拥有良好业绩记录的资深人士。
更严峻的是捐赠基金面临的危机。这是一系列负面情况的叠加。首先,二级市场的下跌和流动性的缺乏,已经让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后,一个客观变量:比如 2025 年可能出现的政治变局,可能会让你彻底崩溃。
这让 LP 们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他们不想失去与 Kleiner Perkins、Index、Founders Fund 这些顶级 GP 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旦中断,就很难再重新建立。所以,当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时,他们会优先保护现有的关系,而不是去投资新的基金。
另一方面,更上层的决策者可能会说,他们想要优质资产,但更不想要流动性差的资产。“流动性溢价(Liquidity Premium)”这个词,在平时毫无意义,但在关键时刻,它意味着一切。当需要钱来资助学生、支付教授薪水时,会被迫出售资产,放弃未来的上涨空间。
关于 Yale 正在二级市场出售价值约 60 亿美金资产组合的传闻,如果属实,那将是一件大事。
背后反应了当前 LP 普遍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人的现金分配规划都出错了。他们没有预料到这场流动性干旱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比 VC 更大的问题是 PE。PE 在捐赠基金中的配置比例要大得多,通常是 VC 的 5 到 10 倍。VC 只是投资组合中的“调味品”,而 PE 才是主菜。当那些 PE 交易在过去几年里都没有实现退出时,造成的现金流压力要比 VC 严重一个数量级。在 VC 行业,某种程度上是在为 PE 受苦。
“分母效应”确实存在,但它不是现在最核心的问题。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有三个层次:
第一,现金模型错了,一切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退出。
第二,不确定回报率是否还能补偿承担的风险和更长的持有期。换句话说,IRR 是否已经下降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灾难性的,尤其对于捐赠基金而言,是现在真的需要钱,因为他们有强制性的资金流出需求。
四、投资者的自我审视与哲学思辨
1. 个人英雄主义 vs 机构化策略
在投资中,一个常见的困境是,当看到一些估值疯狂的热门项目时,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策略而放弃参与。
偶尔有能力参与那些超出自己核心投资范围的交易,如果做对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优势;但如果做错了,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于何时应该破例,有一种非常直接的启发式方法:任何有 100% 信心能获得 5 倍回报的交易,无论所有权和估值如何,都应该去做。这里的核心是“确信”,而不是“想着能赚钱”。即使这笔投资不能让整个基金翻倍,但当进入收益分成模式时,一笔确定的 5 倍回报,如果后续变成 25 倍,将是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益,永远不会后悔。
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在机构化的投资公司里却很难执行。如果一个团队成员向一个 1.25 亿美元的种子基金提议,要写一张三四百万美元的支票,理由是确信能有 5 倍回报,这在管理上是行不通的。这个启发式方法,只适用于可以独立决策的个人投资者,而不适用于团队。
这种差异背后,是个人投资与建立一家公司之间的根本区别。那些愿意进行高仓位投注、投资范围灵活的公司,往往是由单一领导者主导的,这并非偶然。当一个人经营自己的公司时,他可以高举高打,也可以低调行事,不需要遵循固定的模式,可以自己做出例外的决策。这就是为什么像巴菲特那样无需向任何人汇报的投资者,能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因为他可以听取所有意见,然后自己做主。
但在建立一个由多人平等决策的团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在一个有 7 个人可以写支票的团队里,一旦为一个人打破规则,就等于为所有人打破了规则,这会腐蚀整个团队的文化。因此,建立一个有持续性策略的团队,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总会有一些在核心能力圈之外的好交易,不得不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担心的是错过那些完全符合核心策略的交易,比如一个收入在 100 万到 1,000 万美元的 A 轮或 B 轮企业软件公司。错过这样的机会,才是系统性问题的体现。
2. 个人投资方法论
谈及个人投资哲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关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尽管远程办公一度盛行,但湾区的密度优势依然无可替代。
一种非常反常规的投资方式是,完全不做竞争性的尽职调查。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只关注那些增长异常的公司。如果投资的是产品市场契合度之前的早期项目,做竞品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关注的是那些已经在 5 个季度或更短时间内从 100 万增长到 1,000 万收入的公司,那么这样的公司本身就是凤毛麟角。
例如,Talkdesk 在 5 个季度内从 100 万增长到 1,500 万,Algolia 前两年每月增长 20%,Pipedrive 也是其所在领域增长最快的。当只关注增长率处于前 0.1% 的公司时,数量已经非常稀少,根本没有奢侈的选择余地。
在这种严格的筛选标准下,唯一可以妥协的条件就是竞争。只要创始人能在市场中找到巨大的空白空间,无论这个领域竞争多激烈,都可以投资。在这种投资哲学下,有几个条件是绝不妥协的:
基于这些标准,在会见创始人之前,投资决策可能已经完成了 90%。只要市场、增长、团队背景等数据都符合要求,几乎每次在开会前就已经想投了。
归根结底,这种看似极端的投资策略,其商业模式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寻找一个巨大的胜利,一个“奇迹”。投资组合里的其他一切,都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通过严格筛选,投资足够多处于增长率金字塔顶尖 1% 的公司,那么足够幸运的话,其中一个就会成为那个价值 80 亿美元的真正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