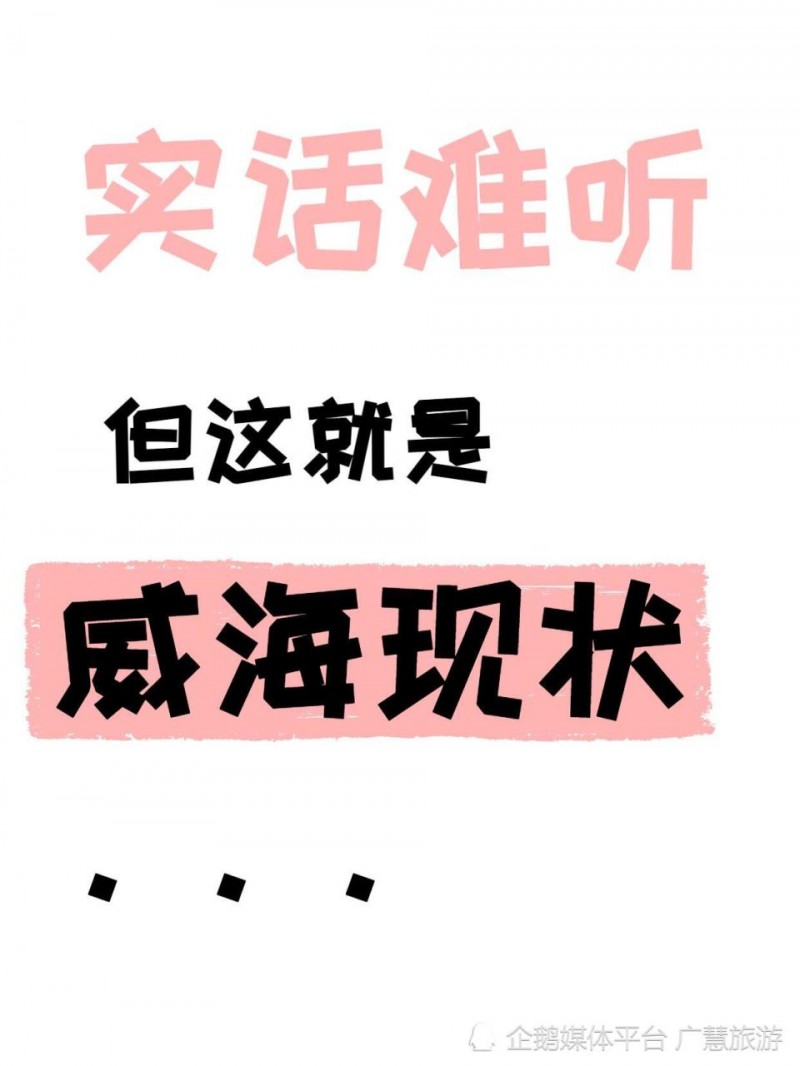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明发展历史中,先民们对遥远外域的探索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当人们对自然的改造与资源利用能力得到提高以后,对更遥远地方和更广大区域的其他人群的交往与交流也在不断地发展。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是人们在获得畜力的支持以后,通过陆路对远方的凿空。从此以后,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上,使节与商旅络绎不绝,佛教的东传,商品的交换,见证了这条道路逐渐走向繁荣。到了隋代,裴矩所作《西域图记》中记载了从敦煌西行至“西海”的北、中、南三条道路,基本覆盖了从河西走廊通过南北疆到中亚、再到西亚中东的广大地区,构成了陆路的贸易网络。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平高昌,击突厥,建安西,设立北庭都护府和诸军镇守捉,使延续自隋朝的丝绸之路更为通畅,“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唐朝与西域诸多王朝和地区往来频繁,主要表现为贡赐与互市。前者多为拂菻、波斯、康国等遣使入贡而唐政府予以回赐,其间往往还伴有使者或随行商旅的商业贸易;后者多为政府组织或民间形成的商品交易活动。在东西之间的官、私交易活动中,粟特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以擅长经商而著称。粟特商人沿陆上丝绸之路东行经商并聚居,其聚居地分布和经商路线大体延续了《西域图记》所载陆行路线:经陆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深入中原内地,与中原文化融合。安史之乱后,受累于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粟特身份,粟特商人受到波及和牵连,加之河西走廊受控于吐蕃,陆路贸易转衰,海路贸易兴起。
受限于驼队贸易的运输能力,加之唐代前期中国制瓷业尚不够发达,隋至盛唐时期粟特商人主导的贸易,以丝绸等较轻的物品和金属、玻璃等珍贵物为主要商品,陶瓷器很少经由丝绸之路运往西域。东西方的交往,造就了文化的传播,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一些西域传来的器皿,如西安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瓶〔图一〕,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7世纪兽首玛瑙角杯〔图二:2〕;中国也生产了许多模仿西域风格的器物。如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667)段伯阳墓出土的巩义窑白瓷仿波斯铜器造型的贴花钵〔图三〕和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带把杯等〔图二:1〕。
图一 玻璃瓶
西安玉祥门外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
上:金筐宝钿团花纹金带把杯
下:兽首玛瑙角杯
图三 巩义窑白瓷贴花钵
西安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
随着丝绸之路(沙漠道)的式微,中唐时期大规模的海上对外贸易肇始了。其实,中国古代先民们通过海路与域外的交往早已有之,至少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如汉书上关于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航程的记载。可知秦汉时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较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个别航程已经可以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都发现了少量可以早到六朝时期的越窑青瓷,但这些都是人员和使节往来时携带的,而不是规模化的贸易行为。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大约始于8世纪后半叶,在晚唐时期(9世纪)得到了迅速发展,10世纪的五代到北宋初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出水陶瓷资料丰富、时间最早的黑石号沉船(Belitung Shipwreck)是一个典型例证。这条沉船的时代正好是中晚唐之交的“宝历二年”(826),出水了57500余件长沙窑瓷器,800余件北方地区的白瓷器,200余件越窑青瓷,和1590多件广东地区产青瓷器。这些瓷器正好代表了从很早开始学界就提出的早期海上贸易的“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实际包括了北方地区多处窑场生产的白瓷器)和广东产青瓷。由于在这条出水众多瓷器的沉船中长沙窑产品占绝对多数,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古代最早大规模外销的瓷器品种。然而,根据学者们对长沙窑的考古学分期研究,长沙窑的烧制时间是从8世纪末到10世纪初,在9世纪的80-9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停烧,兴盛的时间主要在9世纪初到9世纪80年代之间,并不能覆盖整个中唐时期。不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发现,都可以看到在长沙窑兴起之前的8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瓷器就已经开始作为商品销往域外。目前最早外销的瓷器品种是当时在全国瓷器制造体系中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巩义窑的产品,以白瓷、白釉绿彩瓷、三彩器、低温单色釉器物为主。
根据文献记载,巩义窑从开元年间(713-741)率先开始贡官贡御。开元年间可能正是各类手工业品从官府自产转为地方供给的时间,开元二十五年(737)户部厘定各地贡进的物产。瓷器类首先被纳入供送体系的就是巩义窑,而一直被人们强调为北方白瓷之首的邢州所产瓷器并未列入正赋,直到长庆年间(821-824),邢窑的生产进入高峰时期,此时邢窑才与越窑一道列为向中央政府进纳的贡赋。因此,巩义窑是当时的贡御产品,同时也成为最早的瓷器贸易品种。说明最早的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带有官方推动的性质。我们还看到,在巩义窑成为贡御产品的开元年间,也正是瓷器开始通过海路逐渐成为对外贸易商品的时间。关于唐代官方凫海联络外域有一个重要的考古资料: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发现了《杨良瑶神道碑》,记载了宦官杨良瑶的家族渊源与生平事迹。特别是唐朝贞元元年(785)四月,杨良瑶作为聘国使,出使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Abbasid Dynasty)的事件。杨良瑶一行带着国信、诏书,先到南海(今广州),从广州登舟出发,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到达黑衣大食。至少在贞元四年六月之前,使团回到长安。与杨良瑶出使路线相印证的还有“贞元宰相贾耽”(730-805)所著的《皇华四达记》。贾耽在书中记述了当时由唐朝通往域外的七条道路,其中“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唐朝海上交通的重要资料。“广州通海夷道”记载了从广州出发,经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的详细路线,记录了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方向和航行时间,最终到达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杨良瑶出使的时间与《皇华四达记》成书的时间相近,证明贾耽记载的海行路线是与官方的对外交往相关的,《皇华四达记》并非仅仅是一部地理书。
8世纪参与对外贸易的瓷器品种主要是巩义窑所产的白瓷器和唐三彩、白釉绿彩瓷器。白瓷器虽然在海外有广泛的发现,其时代大体为8-9世纪,但中唐到晚唐前期白瓷的考古学分期尚不成熟。学界早就注意到对河南地区中晚唐时期瓷器的分期研究一直是困扰学者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变化并不显著或具有规律性。加之海外发现的白瓷资料发表不充分,故难以靠白瓷来讨论8世纪海上贸易的范围和特点。
唐三彩是辨识度很高的一类陶瓷产品,因此在海外发现的三彩资料大多能引起相当关注,其时代判定也比较成熟,成为我们讨论陶瓷外销肇始的重要资料。巩义黄冶窑是最重要的唐三彩生产窑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窑址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并根据发掘资料开展了考古学分期研究,其中所分第三期是三彩器生产的顶峰期,产品不论数量、种类,还是釉色、图案和装饰手法都非常丰富。该期又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盛唐时期(684-756),釉色常以黄、绿、白三色为主,黄、蓝、绿、白四色釉者不多,贴花工艺在本期开始出现;单彩釉有多种釉色,白釉绿彩器开始出现,但数量较少。常见器形有盆、碗、盘、罐、敛口钵、三足炉等。后段为中唐到晚唐初期(756-840),三彩器与前段相比有所减少,但仍占主流,白釉绿彩器流行;三彩、白釉绿彩、白釉蓝彩和白、黄、绿、蓝等单色釉器更加多样;贴花、印花装饰更加丰富;而常见器形与此期前段相似,有盆、碗、水盂、敛口钵、三足炉等。这里要特别提及白釉绿彩瓷器,根据分期研究的成果,第三期后段即中唐时期,巩义窑流行白釉绿彩瓷器。相关的纪年材料有陕西西安月登阁村唐贞元十四年(798)杜华墓出土的白釉绿彩罐和盘〔图四〕,稍晚一点的还有大同平城智家堡元和五年(810)M90出土的白釉绿彩罐。目前海外发现最早的准确纪年资料是爪哇海发现的唐宝历二年(826)黑石号出水的一批白釉绿彩器物,经过科技检测分析,这些白釉绿彩器是巩义窑的产品。中唐时期白釉绿彩瓷的特点是有大片不规则的釉上绿彩装饰,甚至有时绿彩会覆盖全器。这种风格的器物在越南发现的稍晚于黑石号、时代为9世纪中叶的巴地市沉船(Ba Ria Shipwreck)中就基本不再出水,转而出水较多制作精美的带有印花的绿釉器物,白釉绿彩则发展成带放射状长条形纹理或繁密不规则的绿彩点装饰,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越南发现的“乾符”(874-879)年间的珠新号沉船(Chau Tan Shipwreck)情况与此相同。可见,这类大面积施彩的白釉绿彩瓷主要流行于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初。黑石号沉船是这类器物最晚的纪年资料。从考古资料看,唐三彩在东亚地区有较多的出土。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则少见唐三彩,但发现了较多的白釉绿彩瓷,成为了解西亚中东地区中唐时期中国外销瓷的标志性器物。
图四 白釉绿彩盘和罐
西安月登阁村唐贞元十四年杜华墓出土
从海外出土资料看,自巩义窑的第三期后段,即中唐时期开始,三彩器和白釉绿彩器物开始较多地销往海外;而第三期前段的资料在海外则较少见。日本是最早与中国开展海上交往的域外国度之一,发现的外销瓷比其他地区都要早一些,最晚在唐代初年已经向日本输入了越窑瓷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一件盘口四系瓶,传为奈良法隆寺所藏,根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的记载,此器的时代约为7世纪,为日本船只从中国带回,原来是用于盛装香料。而本文重点关注的三彩和白瓷,有些可以早到7世纪后期到8世纪前半叶。如日本福冈县宗像郡沖之岛第5号和7号遗迹出土三彩贴花长颈瓶瓶口部及腹部残片23件,属于同一个体,口部可复原,为喇叭口细颈状,釉色为黄褐、绿、白三色,腹部残片有凸点状纹饰〔图五〕。复原器形与山西太原金胜村三号唐墓出土的三彩瓶造型和装饰十分相似,此墓年代应属7世纪末至8世纪初,由此推断沖之岛遗迹出土的这件三彩瓶也应属7世纪末至8世纪初。兵库县姬路市加古郡池之下遗迹出土了一件凤首瓶口颈部残件〔图六〕,球腹,推测另一侧有把手,从残存部分尺寸来看,推测器高20厘米左右。颈部细长,釉面剥蚀严重,釉色为棕黄釉、绿釉、白釉,报告推测年代为8世纪前半期。造型与神龙二年(706)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褐釉凤首壶相似,可作为印证。池之下遗迹附近有港口相关设施,这里出现的唐三彩或与遣唐使的活动有关。三重县绳生废寺出土了一件三彩印花碗,出土时与一件滑石质罐相搭配〔图七〕,这组器物亦可早到8世纪后半叶的中唐时期。日本出土最具特色的唐三彩是数量众多的小型长方形瓷枕残片,出土遗迹多达三十余处。奈良市大安寺出土的三彩枕尤多,残片多达400余片〔图八〕。从窑址发掘资料看,这种枕的生产从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晚唐,大安寺出土的这些三彩枕应主要于8世纪输入,且以8世纪后半叶居多。早期唐三彩的传入,大部分是遣唐使带回。综上,日本由于与唐王朝的特殊关系,从盛唐后期到中唐时期就有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输入,并且数量递增,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模式。另外,在日本的数个遗址里出土了三彩三足炉残件,不少带有贴花装饰,如福冈县太宰府市太宰府史迹观世音寺;奈良县西大寺旧境内平城京右京一条南大路;大阪府东大阪市若江南町2丁目若江废寺遗迹等,这些三足炉与巩义黄冶窑出土器物相同,为该窑产品,主要流行于8世纪。同样,日本也发现了一些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的白釉绿彩瓷,此处不再罗列。到了晚唐时期,日本境内发现的中国陶瓷与在其他地区遗迹中出土的器类相似,已是作为商品外销进入日本。
图五 三彩贴花长颈瓶残片及线绘图
日本福冈县宗像郡沖之岛第5号和7号遗迹出土
图六 三彩凤首瓶口颈部残件及线绘图
日本兵库县姬路市加古郡池之下遗迹出土
图七 带三彩盖滑石罐
日本三重县绳生废寺出土
图八 唐三彩瓷枕
日本奈良大安寺遗址出土
朝鲜半岛虽然与唐朝陆地相连,但通过海路与半岛南部的联系早在汉代就已十分发达。从六朝时期开始,在今天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发现了越窑瓷器,最早的可以上溯到两晋时期,自两晋时期到唐代相延不断。如传开城遗址出土的青瓷虎子,早期输往朝鲜半岛的还有不少越窑青瓷羊形器,韩国庆州雁鸭池遗址出土越窑瓷片则可作为唐代后期越窑输出的典型代表,尽管文献记载雁鸭池的始建年代是674年,但该遗址所出越窑瓷器均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且以晚唐为主,说明越窑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输出是持续不断的。输入的渠道应主要通过海路,因此8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也发现了不少唐三彩和白瓷器,大部分都位于新罗都城所在的庆州地区,表明其输入可能带有官方色彩。如韩国庆州朝阳洞遗迹出土的带蓝彩的三足炉〔图九:1〕,与巩义窑三期后段的三足炉十分相似〔图九:2〕;在庆州萝井祭祀遗迹中也出土了两件造型相似、但带有贴花装饰的三彩三足炉残片;庆州九黄洞皇龙寺遗址中出土的两件三彩带弦纹残片,应为弦纹三彩长颈瓶的产品。这种长颈瓶与懿德太子墓以及太原金胜村三号墓中出土的长颈瓶造型相近,时代为8世纪前半叶。在新罗王京遗址也出土了数片与日本大安寺相同的三彩瓷枕残片〔图十〕,这些出土资料证明,朝鲜半岛出土中国瓷器数量较多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中唐时期,甚至盛唐后期,即8世纪,与日本相似。9世纪以后数量进一步增加,瓷器种类与其他地区趋于一致。
图九 韩国出土唐三彩与巩义窑产品对比
左:韩国庆州朝阳洞遗址出土唐三彩炉
右:巩义黄冶窑址第三期后段地层出土三彩炉
图十 三彩瓷枕残片
韩国新罗王京遗址出土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是早期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目的地和中间港。这里发现的中国瓷器具有与环印度洋地区十分相似的面貌。东南亚地区也曾发现过一些早至六朝时期的越窑瓷器,但数量不多。而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区域尚未发现早于唐代的中国瓷器。中唐时期开始发现了一些北方地区的瓷器。冯先铭曾著文介绍泰国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thammarat)地区出土了唐代陶瓷标本700余件,包括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广东地区青瓷等,还有一件三彩盅残件,此外还有一些伊朗绿釉陶片,但并未刊布照片。谢明良在其《中国古代铅釉陶的世界:从战国到唐》的引文中称,泰国国立博物馆B. Chandavij表示,泰国境内出土唐三彩的遗址至少有三处。由于这些资料均未公布照片,所以无法判断其时代。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Sumatra)岛南部巨港(Palembang)的勃姆巴鲁(Boom Baru)遗迹中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器,其中包括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北方白瓷、广东青瓷等,此外还有三彩和白釉绿彩产品〔图十一〕。巨港是唐代文献中所记室利佛逝(Sriwijaya)王国的都城,是海洋贸易的中间港,在7-13世纪的地区和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成为中间港,要有一定规模的库房,以存储来自四面八方的货物,并有较大的货物流通量。巨港通过穆西河(Musi River)与马六甲海峡相连,河床中出土了不少中国陶瓷器。巨港的室利佛逝博物馆收藏有大量长沙窑瓷器,也有部分早到中唐时期的瓷器,如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巨港出土的中唐时期酱釉净瓶,亦为巩义窑产品〔图十二〕。穆西河畔的民间盗捞十分猖獗,Kitchener D. J.等人就报告过一些唐三彩和白釉绿彩瓷器。同样位于马六甲海峡岸边的占碑也出土过一些唐三彩器物和其他中国瓷器,如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罐,时代甚至可以早到盛唐后期〔图十三〕。
图十一 唐三彩和白釉绿彩瓷瓷器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勃姆巴鲁(Boom Baru)遗迹中出土
图十二 酱釉净瓶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出土
图十三 唐三彩侈口罐
苏门答腊岛占碑市出土
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藏
编号:INV.3050
于永健摄
马六甲海峡以西的环印度洋地区,包括了西亚和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是大规模海上贸易兴起以来才开通的海上贸易航线。这个区域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瓷器大体可以代表海上贸易全面兴起的时间。目前在环印度洋地区基本未见可以早到盛唐时期的中国瓷器。考古资料比较充分的有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Mantai),位于斯里兰卡西北部马纳尔地区,坐落于临海滩地上,是一座椭圆形双重城垣城址。该遗址是古代印度洋航线上的重要港口遗址,在8—9世纪时期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间港,957年曼泰被斯里兰卡北部人群(The Cholas)摧毁。这里的发现对于了解古代中国与环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980-1984年,英国考古队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2013年出版了考古报告,其中刊布了两件唐三彩残片〔图十四:1、2〕,大英博物馆还保存有一部分英国考古队发掘曼泰遗址出土的标本,其中有一片钴蓝釉釉陶片〔图十四:3〕,这三件标本都具有明显的8世纪后半叶中唐时期的特点。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白釉绿彩瓷片,有一些带有明显中唐时期风格〔图十五〕。2018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凯拉尼亚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曼泰港遗址北部进行了考古调查。2019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获得了一些早期的标本,包括一件巩义窑白釉饼足碗〔图十六〕和三片唐三彩瓷片〔图十七〕,时代都可以早到中唐时期。
图十四 唐三彩残片
英国考古队发掘斯里兰卡曼泰遗址出土
1、2. 唐三彩残片 范佳楠摄
3. 钴蓝釉陶片 张然提供
图十五 中唐时期白釉绿彩瓷片
英国考古队发掘曼泰遗址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编号:2007,3027.183
范佳楠供图
图十六 中唐时期巩义窑白瓷碗
四川大学考古队发掘曼泰遗址出土
范佳楠供图
图十七 唐三彩标本
四川大学考古队发掘曼泰遗址出土
范佳楠供图
曼泰遗址作为穿过马六甲海峡以后前往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交通节点,出土的这些标本与中东地区发现的中唐时期的中国瓷器大体相同。传出土于埃及福斯塔特(Fustat)遗址的两件唐三彩器物,现藏于意大利法恩莎国际陶瓷博物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 in Faenza),其中的一件印花三彩盘的残片〔图十八〕,其上的压印宝相花装饰在巩义窑第三期前段,即盛唐时期就已出现并流行,并在第三期后段的中唐时期依然流行,但这件残片上使用了钴蓝彩,宝相花以外的部分是白釉,未施装饰,具有8世纪后半叶的特点,属于中唐时期较早阶段的特征。谢明良特别考证了这件器物,指出其可能并非出土于福斯塔特遗址。笔者对此也表示赞同,因为迄今在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大体都是9世纪第二个25年以后的。实际上,是否是福斯塔特出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出土于中东地区,体现了中唐时期中东的贸易情况。三上次男还曾提及福斯塔特出土有唐三彩瓶及盆、碟残片,惜未见照片。
图十八 唐三彩印花盘残片
传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
意大利法恩莎国际陶瓷博物馆藏
伊拉克萨马拉遗址是西亚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代城市遗址,其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南距巴格达125公里。由于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与巴格达民众的冲突,阿巴斯王朝于836-892年迁都至此,有八位哈里发在萨马拉就任。1911至1913年德国弗里德里克·扎勒(Friedrich Sarre)、恩斯特·赫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在此发掘了哈里发王宫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唐代瓷器。德国考古队发掘出土的部分资料现存柏林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 Museum),其中有两件三彩印花碟〔图十九〕与越南发现的巴地市沉船出水的器物风格相似,另有白釉绿彩碗和盘各一件〔图二十〕,都具有明显的9世纪中后期的晚唐时期的特征。以上四件标本都已明确标明出土于哈里发王宫遗址。其时代与萨马拉为阿巴斯王朝都城的时间相符。佩加蒙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三彩贴花小罐和一件三彩小碗〔图二十一〕,它们并非哈里发王宫遗址发掘出土,但出土于萨马拉遗址,这两件三彩器具有明显的中唐时期的特征,时代为8世纪末到9世纪初。萨马拉遗址还出土了具有8世纪风格的白釉绿彩瓷〔图二十二:2〕。英国杜伦大学收藏的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在20世纪后期调查伊朗南部锡尔詹地区所采集的中国瓷器标本中也有一些可以早到中唐时期的白釉绿彩瓷标本〔图二十二:1〕。以上资料证明,在中唐时期,特别是中唐时期较晚的阶段,即8世纪末到9世纪初,中国瓷器通过海上贸易渠道已经运销到了环印度洋的西亚、中东地区。
图十九 三彩印花盘
萨马拉哈里发王宫遗址出土
德国佩加蒙博物馆藏
左:馆藏编号I.5371
右:馆藏编号I.4945
图二十 白釉绿彩碗、盘
萨马拉哈里发王宫遗址出土
德国佩加蒙博物馆藏
图二十一 唐三彩小罐、小碗
萨马拉遗址出土
德国佩加蒙博物馆藏
图二十二 白釉绿彩瓷标本
左: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锡尔瞻地区所采集的白釉绿彩瓷片
右:美国密歇根大学藏萨马拉遗址出土白釉绿彩瓷片
李旻供图
8世纪末中国瓷器销往西亚、中东地区最引人瞩目的是文献记载的一个事件。伊斯兰历178年(794),为平息呼罗珊(Khorasan)、花剌子模(Khwarazm)、锡斯坦(Sistan)及河中地区(Transoxania)等地的叛乱,哈里发哈伦·拉施德(Harun al-Rashid)命法泽尔(Fazl)担任这一区域的总督。两年后法泽尔卸任,哈里发任命阿里·本·艾萨( ‘Ali b. ’Isa b. Mahan)接任呼罗珊总督。这位继任的管理者被指控谋反,为获得哈里发的认可,在其领地内横征暴敛,搜刮大量奢侈品以进贡给哈里发,贡品的数量与珍贵程度为历任总督难以企及。波斯文献——《贝伊哈奇史》(, The History of Beyhaqi)记载了这一事件。贡品包括当地与周边国家生产的各类珍贵丝织品,贵金属制作的甲胄与装饰华丽的坐具,各类宝石与珍珠,奴隶以及200件中国生产的官用瓷器(chini faghfuri),包括大盘、杯等品类,均制作精良;另外还有2000件其他种类的瓷器,包括水杯,水注,不同大小用于盛酒的罐子及其他品类。译者进一步解释,在历史学家Tha’alebi所在的年代,即10-11世纪,“sini”或“chini”长期被用来指代此类精美的瓷器。由于阿里向哈里发贡献物品的事件在历史上十分著名,有多部文献对此事有过记载。
这条文献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在阿里·本·艾萨治理呼罗珊的8世纪末到9世纪初时期,在中亚地区有大量的中国瓷器,甚至包括天子所用的精美瓷器。根据上文所述,长庆年间(821-824)以前贡官的主要是巩义窑瓷器,应该包括了白瓷、白釉绿彩瓷和三彩器。所以,在阿里进纳的2200件瓷器中,可能大部分是巩义窑的产品。第二,阿里·本·艾萨治理所进纳的瓷器主要来自呼罗珊地区,根据《贝伊哈齐史》记载,阿里搜刮宝物的范围还包括了河中地区,伊朗的里海南部沿岸地区塔巴里斯坦(Tabarestan)、锡斯坦(Sistan)、拉伊(Ray),戈尔甘(Gorgan)及伊斯法罕(Isfahan)等伊朗中部及西、北部的广大地区,还有阿富汗的尼姆鲁兹(Nimruz)、锡斯坦(Sistan)等地。这一区域既有中亚的内陆地区,也包括了比较接近波斯湾和马六甲海峡等海路节点的地区。据此判断,在呼罗珊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中唐时期瓷器有可能是从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运销而来的。即粟特人主导的丝绸之路沙漠道贸易网络和阿拉伯人主导的海上贸易网络共同构成的,海路则是到达波斯湾或马六甲海峡的室利佛逝王国后经过陆路向波斯的内陆地区运送。
8世纪后半叶中国与波斯地区交往与贸易还有一些沉船资料的证据。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发展,近些年发现了数条8-9世纪的沉船。目前发现这一时期最早的沉船是泰国沙没沙空省(Samut Sakhon)距暹罗湾8公里的塔钦河河道中的帕侬苏琳沉船(The Phanom-Surin Shipwreck),根据碳十四测年的结果,其时代大体是8世纪中后期。可惜帕侬苏琳沉船因沉没于内河,货物有机会在船废弃以前搬走,所以出水的器物较少,以陶罐和广东产青瓷罐残件为主,很有可能是广东封开窑生产的青瓷罐。可以确认这些罐用于盛放稻子和用作船体密封料的沥青〔图二十三〕。这不仅证明在8世纪中后期,广州作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其周边地区开始生产青瓷器,并且以生产海上贸易的关键器具——储物罐为主要产品,这些青瓷器也是最早参与海上贸易的中国瓷器;其船体构造显示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缝合船,用以开展远洋贸易。印证了8世纪中国与中东地区海上贸易的肇兴。
图二十三 泰国帕侬苏琳沉船出水的8世纪后期广东产青瓷储物罐
9世纪以后,中国瓷器的外销规模逐渐扩大,从东亚日本、韩国的众多遗址,印尼爪哇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越南发现的巴地市沉船、珠新号沉船,到西亚、中东乃至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同时期的遗址中都发现了中国瓷器,10世纪瓷器外销进一步发展,从销售的范围到规模都有了扩展,地点已延伸到非洲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达到了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第一个高峰。
综上所述,通过对域外遗址和沉船出土中国瓷器的观察和文献资料的收集,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陶瓷作为商品大规模对外销售的时间大约始于8世纪,即盛唐后期到中唐时期。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由于遣唐使等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地缘优势,发现了一些8世纪前半叶的标本,少量可以前推至7世纪末期。而东南亚地区以及环印度洋地区最早的标本主要属于8世纪末期到9世纪初,即中唐较晚的时期。这与收集到的一些文献资料的时间相吻合。
第二,早期的外销瓷器主要是最早进入官方供送系统的巩义窑瓷器,包括白瓷器、三彩器和白釉绿彩瓷,此外还有少量在广州港周围地区生产的广东青瓷,以各类储物罐为主。巩义窑输出的规模还比较有限,海外发现的外销瓷凤毛麟角,沉船也只有帕农苏林沉船一条。真正大规模向外输出陶瓷产品的时间出现在中唐末到晚唐时期,此时长沙窑、越窑、北方白瓷和广东产青瓷都大量参与到了外销的行列。
第三,最早的陶瓷外销带有一定官方推动的特点,有可能最早的瓷器外销有一部分通过陆路输出,由官府认可的粟特商人承担,但很快就转变为海路外销为主,在中唐后期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陆海并行的外销模式。到晚唐时期,就基本上全部通过海路外销了。